◎姜贻斌
他几乎是一个人待在家里,打发这漫长的时光。
平时不怎么爱卫生,在别人眼里,家里简直像个垃圾站,东西乱摆,没有章法。地板上的书籍、纸屑、果皮、空盒子,像海洋上零碎的岛屿。家具上蒙着极薄的灰尘,像时光的沉淀物。阳光无声地斜射进来,灰尘似乎又添加上一道年轮。他却疏于打扫,觉得无伤大雅,最多是顺便将垃圾带出去,并没有刻意而为之。他甚至自我安慰,自己家里比某些年轻人来说,应该算讲究卫生的模范了。从电视上,就可以看到某些年轻人租的房。租的房里垃圾堆积如山,方便面袋子、食品袋子、快餐盒子、酒瓶子、烟盒子等等,简直无法插脚,像千山万壑的微型版。还有许多蟑螂窜来窜去,像个很久也没有清理的垃圾站。他们甚至遭至房东的严厉呵斥,叫他们立即搬出去。租客却毫无反应,半听不听,仍然懒散地躺在床上玩手机,脸皮真是太厚了。自己家里还不至于如此吧,只是不那么整洁罢了,只是有点灰尘而已。
因此,他有一种强烈的比较,也有一种胜者的傲然。因为家里少有人来,只要自己不产生丝毫生理上的反感,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他甚至坚持自己的测试标准,那就是经常用鼻子在空中闻一闻,似乎在判断是否有异味——这已然成了他自测卫生的手段和习惯。当然,他也不像某些00后的租客,会遭至房东严厉的指责。那张宽大的床铺,在床头雕花的实木上,虽然蒙有一层淡薄的灰尘,却也无伤大雅。对此,他视而不见,也没有清扫过。被子和枕头像两个弃儿,堆砌、萎缩,显得可怜巴巴。当然,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,却也说不上冤枉。
他历来反感那些天天辛苦搞卫生的男女。他们每天清早起来,不辞辛苦,弯腰拖呀拖地板,擦呀擦桌椅,抹呀抹饮具,似乎要把家里弄成宾馆样式,要把自己装扮成典型的家庭劳模,以获得家人们的喝彩。在他看来,这类男女要么是有洁癖,见不得一粒灰尘,要么是精神空虚,因为无事可做。他们的任务就是打麻将(早上谁打麻将呢),要么是跳舞(距离公园太远,附近的广场舞,又要等到晚上),所以,趁着寂静而无聊的早晨,卖力地进行体力劳动,以填补那段时间的空虚。这类男女甚至美其名曰,这样既搞了卫生,又锻炼了身体。
这当然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,他无权干涉或劝阻。说不上欣赏,也说不上反感。谁愿意当家庭劳模,谁就去当吧,他不需要这顶貌似光彩的帽子。
他虽然退休了,却总是觉得还有许多做不完的事情,好像在跟时间赛跑。他觉得这个比喻很准确,自己就像个马拉松运动员,从年轻时就开始跑步,不停地朝着那个终点奔跑。虽然气喘吁吁,满头大汗,甚至腰酸背痛,四肢疲软,但似乎仍有足够的体能,目光紧紧地盯着前面的目标——尽管那个目标有点虚幻,甚至还看不见踪影。
他是个较有影响的学者,尤其是对地方文化有所研究和建树。因此,他每次提出的观点,总是那样尖锐、新颖,甚至刻薄,让人思考。他似乎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,滔滔不绝,声音洪亮,其观点又能够让人眼睛一亮,触动心绪,颇有心得和启发。尽管他已经不在正式的舞台上了,而在舞台下面,他仍然像个高级的、引人注目的吹鼓手或批评者,仍然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,让人不可小觑。因此,许多地方照样请他去讲课,或邀请他去参观,或敬请他对某地的文化建设提出不同凡响的建议,等等。当然,这种社交活动,一般只有三五天而已,吃了,喝了,该讲的话也讲完了,该交出的方案也交了,然后,又回到自己家里,做个安静的隐士。如果没有外出,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脑前,不是做方案,就是查资料,或整理自己的文集,或给某个弟子做序,等等。
当然啰,还要记得按时吃药。其实,他的身体也不是有多大的问题,只是血糖稍稍有点超标而已,不太碍事,平时只要注意忌口就可以了。他担心忘记吃药,便把药瓶摆放在电脑边上,这样能够提醒自己。当然,还要摆上烟和茶杯。至于吃饭问题,他不太讲究,一般不动手做饭,经常下楼去街对面的小饭馆解决。如果吃早餐,一碗面条便可草草打发。如果是中晚餐,兴致来了,就会叫上两个菜。他最喜欢吃酸萝卜炒新鲜猪大肠,加上一份鲜嫩的木耳菜,然后,从纸袋里摸出一瓶酒,一只银色的小酒杯,举杯独饮。他喝得很自在,也很悠然,不紧且不慢,完全忽略了周围的嘈杂声,还有马路上像流水线驶过的车辆,一味沉浸在自我陶醉的世界里。
当然,这种状况并不是很多,因为有许多人请他吃饭,喜欢听他侃侃而谈,指点江山。也不知是从哪天开始的,别人都喜欢听他说话。他说话既幽默,又通俗易懂,完全没有那种让人沉闷的学究气,或之乎者也之类,更没有那种装逼的感觉。因此,许多人愿意跟他一边喝酒,一边听他聊天,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、轻松、有趣。而且,那些人晓得他的生活习惯,中午一般不出去吃饭,因为他起床很晚,一般要到十点多钟才起来,如果中午出去吃饭,那就太耽误时间了,下午根本就做不成事了。因此,要出去也是在晚上。他觉得这样轻松许多,白天既做了事情,晚上又补充了能量,何乐不为?他可不想做那种苦行僧。也许是他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吧,也许是他比较顾及自己的身体。细细一想,如果身体不好,即使想做点事情,也是做不到的。这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痛苦,还会给家人带来麻烦和负担,实在没有这个必要。他不会像某些人那样,已经躺在病床上了,还拿着一块木板架子垫着,上面摆上手提电脑,仍然在辛勤地劳作。他不会这样做,他要以自己健康的身体,傲然地行走在世界上,以至走完短暂而漫长的一生。
况且,他的酒量也不输别人,每次喝完二三两白酒,还要用冰啤漱口。这让在座的年轻人目瞪口呆,因为他们都不敢喝混合酒,也不敢喝冰啤,便伸出大拇指夸赞,因此,每每让人惊讶不已。人们纷纷赞道,肖教授可以呀,竟然是混合双打冠军呀。他听罢,极其兴奋,左手夹烟,右手握着酒杯,得意地说,倒——酒。颇有几分豪气。喝罢酒回家,如果喝得有点多,便躺下来睡觉,慢慢进入梦乡。如果喝得不多,没有多少醉意,那就靠在床头看书,抽烟,喝茶,或是回复微信,很是惬意。
他不是孤家寡人吧?
当然不是。
老婆在南京帮着带孙子,孙子叫固然。他每天几乎都要跟孙子视频,逗逗乐。孙子长得很可爱,两只眼珠,又圆又大又亮,头发卷曲,简直像个洋娃娃。除了在电脑前工作,跟孙子视频,也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。他几乎在每天下午四点左右,准时跟老婆视频,然后,跟孙子说说话。孙子叫他爷爷,他高兴得不得了,甚至手之舞之。每次到快要结束视频时,他还要孙子跟他亲一个。虽然隔着手机屏幕,他却感到孙子的吻是贴着自己脸上的,甚至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温暖。儿子说,他准备还要生一个。他回答说,生,生,生,你难道没有看见人口在下降吗?
以往每到快要过年了,他才去南京跟家人团聚,享受天伦之乐。他每天逗着孙子玩耍,仿佛又回到了儿时,笑声不断。他甚至四肢卧地,让孙子骑在自己背上,做骑马状,嘴里发出笃、笃、笃的声音,在地上不停地转悠。春节那几天,他还是要休息一下,暂时与电脑告别,最多是看看书而已,让阳光静静地铺展在自己身上。或是跟儿子痛饮几杯,或者跟随家人们外出游玩。过完年,又回到自己家里,马上进入工作状态,进入一个安静的世界。
今年则有所不同,儿子说要回来过年,还说固然有三岁了,可以带着四处走走了。他听罢,当然很高兴,至少可以让这个寂静的家里多些欢笑声。却又有某种措手不及的感觉,因为家里突然将要回来这么多人,需要吃很多的饭菜。他便对儿子说,那我要准备一些菜吧。儿子说不要他操心,他已经点了许多菜,都是外送,只需要他在家里接货就是了。他想这也可以,免得让自己操心。
所以说,他虽然是个空巢老人,却丝毫也没有孤独的感觉,因为他精神上很充实,似乎有做不完的事情。
好几次,老同学联系他,叫他出来参加同学聚会。他不便拒绝老同学的好意,终于去参加一次。谁知却让他大失所望。因为那些男女同学,竟然没有一个喝酒的,不是说自己有脂肪肝,就是说自己有严重胃炎。他们甚至在饭桌上,拿出花花绿绿的药片、药丸,以及水剂,频频往嘴巴里送,好像他们不是来吃饭的,而是来吃药的,或者说,是来搞药品展览的。他们并且郑重声明,他们绝对喝不得酒,烟酒害人,并且,好心地劝他也不要喝酒,不要抽烟,还说是身体第一。况且,我们都能够活到现在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,还要对家人负责。言之凿凿。他听罢,莞尔一笑。他当然明白身体第一,同时,也感到索然无味,怔怔地望着他们发呆,像已有老年痴呆症。他好像不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,而是来发呆的,因此,情绪极其低落,独自喝了几杯酒,便悄悄抽身离去。
除了他,这些老同学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,因此,他们很早就进了工厂上班,而且,都是县里的小企业,所以,两者的差距过于明显。他们谈论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话题,谈论退休工资多少,住院能够报销多少,孙子的牛奶粉每个月需要多少钱,等等,简直喋喋不休,像一窝叽叽喳喳的老麻雀,还在垂死吵闹。因此,他对这没有半点兴趣,也插不上话,便独自默默喝酒,似是对他的一种惩罚。尤其让他感到气愤的是,他出于一片好心,听到许多同学经济极其拮据,便提出把所有的费用包下来,包括吃饭、唱歌、住宿,甚至路费。谁料竟然遭到一片嘲讽,说他是在显势,说他根本就看不起同学们,还说他在故意摆谱,等等,总之,十分之难听。因此,他没有等到聚会散去,便悄悄提前走了,甚至连个招呼也没有打。后来呢,干脆不再参加这类聚会了,甚至退出同学群。他可以猜测到,自己得罪了许多人。又想,得罪就得罪吧,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也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,他乐于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,阅读、写作、思考、喝酒、抽烟、喝茶。他甚至在记事本上,记录着一些需要做的事情。比如,哪天外出讲课,哪天外出参观,哪天做方案,哪天见某人,等等。总之,他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,丝毫也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。他也不像某些业界的人,没有自知之明。比如说吧,对方并没有邀请某某,某某却四处打电话,或托熟人说情,叫对方邀请自己去讲课,并且,要先把讲课费确定下来,以及接送的时间和地点。还有的人更可笑,如果对方邀请他去开会,他要让对方先把会议议程发过来,说他要有所准备。其实呢,他是在查看出席会议的名单排列,如果自己排在后面,他就要大加生气,说一定要把他排到前面来,另外,还要将一些头衔加上去。甚至愤怒地说,某某为什么排在我前面?他又算哪根葱?他不就是一个委员吗?如果不把某某移到我屁股后面,我就不来参加活动了。每每听到这类事情,他便微微一笑,小骂一句,娘希匹。嗤之以鼻。
还在十多天前,儿子来电话,说他们要回来过年,想到他一个人长期待在家里,又不喜欢打扫卫生,屋里肯定比较邋遢,很不利于健康,尤其还有孙子固然。儿子说,他可以联系保洁员来家里打扫卫生。他听罢,默认了。他虽然不喜欢家里来人,却也不反对搞卫生,尤其是全家要团聚了,卫生还是要讲究点吧。他却提出一个要求,叫儿子必须严格规定时间,那就是,保洁员在家里逗留的时间,绝对不能超过四个小时,因为这是他能够容忍的极限。
他耐心地解释说,他不喜欢陌生人在家里逗留的时间太久,即使有人来家里找他谈事,也绝对不能超过一刻钟。总之,他喜欢家里那种安静的感觉,那种感觉让人舒服、自在、任性,不喜欢有人打破这种安静,因此,他希望这种安静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。这一点,他已经做到了,因为这是他的家,他说话算数。
当然,如果在饭店或茶馆谈事,那另当别论了。酒喝完了,茶也喝得入境了,事情呢也谈成了。按说吧,一般请人搞家庭卫生,至少需要八个小时,而且,得有两个人前来服务——那么,这就越过了他的底线。当然,儿子清楚他的生活习惯,理解地说,那就请四个小时的吧,来一个保洁员可以吗?他点点头,说,可以。
儿子与他约定了时间,第三天下午保洁员来家里搞卫生,意思是让他有点思想准备,而且不要外出。不多时,儿子便发来保洁员到家里搞卫生的准确时间,并且,叫他不要关机,保洁员随时要跟他联系。他一看,搞卫生的时间是第三天下午一点到五点。他认为这个钟点还比较合适。因为他起床很晚,一般要到上午十点多钟才起来,中午不睡觉,上街随便吃点东西便开始工作。所以,这对他并没有多少影响,如果晚上有饭局,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他每次外出吃饭,一般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出门。或对方来车子接,或自己打个的。因此,他对儿子解释说,他虽然不会关机,却喜欢静音。其实,到第三天上午,他并没有按下静音键,担心对方联系不上自己。
第三天中午十二点五十五分,他的手机响起来了。
他估猜是保洁员,却还是问道,是谁?
对方是个女人,说,我是来你家搞卫生的,我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
他走出书房,迅速地打开房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中等个子的女人,拖着灰色工具箱,戴着紫色口罩,穿着棕色薄羽绒服。头发蓬松,眼窝很深,像个广东女人,估计年龄在四十岁上下。他礼貌地请她进来,说,这就要辛苦你了。女人走进来说,应该的。他说,要换鞋吗?说出这句话,他心里有点发虚,因为家里并不怎么干净。女人解释说,我自己带鞋子来了。等到女人走进来,他指着屋里自嘲地说,我这个家里呀,应该是天下最脏的了。
女人松开拉箱,淡淡地说,未必。
未必就未必吧。然后,他回到书房,坐在电脑前准备继续工作。
这时候,女人轻轻走到书房门口,说,请问先搞哪里的卫生,你家的主卫生区呢?
他不由愕然,似乎一时没有听明白,怔怔地望着女人。难道还有主卫生区这个说法吗?他真的不晓得,便敷衍地回答说,你随便从哪里开始吧。他想,书房到最后再搞也不迟,趁这个时间,还可以工作一下。
女人淡定地站在书房门口,解释说,因为只有四个小时,所以,我也只能迅速地打扫一下,至于玻璃、窗帘等等,那就搞不赢了。话语里似乎有一丝歉疚。
他明白她所说的迅速打扫一下是什么意思,大大咧咧地说,没有关系。又望着她说,你也没有必要戴口罩,摘下来吧,太不透气了。他平时就很烦戴口罩,不需要戴的时候他坚决不戴。
女人说,我到别人家里,对方都要求戴口罩,甚至还要检查健康码。女人的意思是,像你这样警惕性不高的东家,她还没有见过。
他笑了笑,说,我看没有那个必要吧。
女人没有听他的,仍然戴着紫色口罩,似乎这是她的底线。
家里为三室一厅,两卫一厨,面积并不大,却也不小,一百五十平米。他觉得这已经很理想了,没有必要像有些人搞几百平米,家里空得像没有香客的寺庙,冷清极了。其实,人生只不过是三尺床而已,实在没有必要住几百平米吧,那无非是显势罢了。
女人开始在其他房子打扫,发出轻轻的声音。他觉得,这种声音并不影响他的思路,他边抽烟,边喝茶,边打电脑,间或还接个电话,或回信息。想象着家里马上就要旧貌变新颜了,他似乎有点得意,因为这是迎接家人归来的前奏曲。当然,自己也不必像个监工,不时地去查看人家的进度,以及是否打扫干净了,那实在没有必要,就让人家去打扫吧。虽然,跟这个女人是第一次打交道,也没有多少交流,他却很喜欢这个女人,说话干脆利落,并不拖泥带水,而且,打扫起来不声不响,轻手轻脚。听说有的保洁员在别人家里像大闹天宫,发出砰砰叭叭的声音,令人极其烦躁。似乎是对主家的某种抱怨,也似乎是对目前生活的不满,现在要发泄在主家头上。
他望着电脑,心想,如有必要,下次还要请她过来,因为熟门熟路了。他小心地把女人的手机号码保存下来,注明保洁员,后面还打个括号,括号里写个女字。他在猜测,不知她老公是否也在这个城市,也不知她老公是做什么的。当然,也不知她有几个子女,子女读几年级了。他想罢这些问题,还在想着另一个问题。如果在夏天,女人穿得很少,不知是否会引起自己的兴趣,如果双方中意的话,说不定还可以云雨一番,至少在家里很安全。想想,又自嘲起来,哎呀,自己怎么能有这种龌龊的念头呢?真是该死。他拂掉杂念,专心打字,他要在年前帮某个地方做个大的方案,然后,好好地休息几天。
时间过得很快,女人的手脚也很快迅、利索。这时,女人悄悄来到书房门口,手里拿着一个小巧的黑色遥控器,问,这个遥控器还要不要?这是很早的东西了。
他叫女人拿过来一看,原来是个老遥控器,样式丑陋,早已淘汰了,也不知她从哪个角落找出来的,便说,丢掉吧。
女人点点头,走了出去,继续搞她的卫生。
他呢,继续专注精力,做着手头上的这个大方案。他认为,这个大方案,一定会叫那个地方上的官员大为惊喜,他们绝对想不到,他竟会有这种大思路和大气魄。他自己也认为,这个方案是近年来,自己做得最好的。当然,这也跟那个地方的地形、资金,文化底蕴以及认知水平分不开。因此,他心里感到很愉快,噼里啪啦敲着键盘,似乎眼见着方案已成现实,渐渐地出现在他眼前。做了一阵子,信息来了,嘀一声提醒他。他拿起手机一看,原来是朋友请他吃饭,并且,把时间和地点发了过来。他当即回复,收到,谢谢。
他觉得做成一个理想的方案,需要具备某些条件,不然,是无法实现的。更重要的是,需要地方上落实在行动上,才不会成为空谈。
他正在想象着地方上的官员对他的方案赞赏不已,女人又来到书房门口,举起一个空酒瓶说,这个可以丢掉吗?空的。并且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它。
他一看,是个造型极其好看的瓷质酒瓶,呈金黄色,四周雕着腾云驾雾的龙。不说酒吧,光是这个酒瓶就造价不菲。他却不记得是哪次喝酒带回家的,因为它实在太好看了,即使做个摆设也不错,如果插上鲜花,那就更有味道了。只是他拿回家后,就随便将它弃于沙发脚下,既没有插上鲜花,也没有将它作为摆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一种浪费。
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,嘿嘿,我倒是忘记了,还是丢掉吧,反正也没有什么用。心里还是嫌这个女人有点啰唆,其实,这些东西不值得都来问他。
女人嗯一声,无声地离开了。
(节选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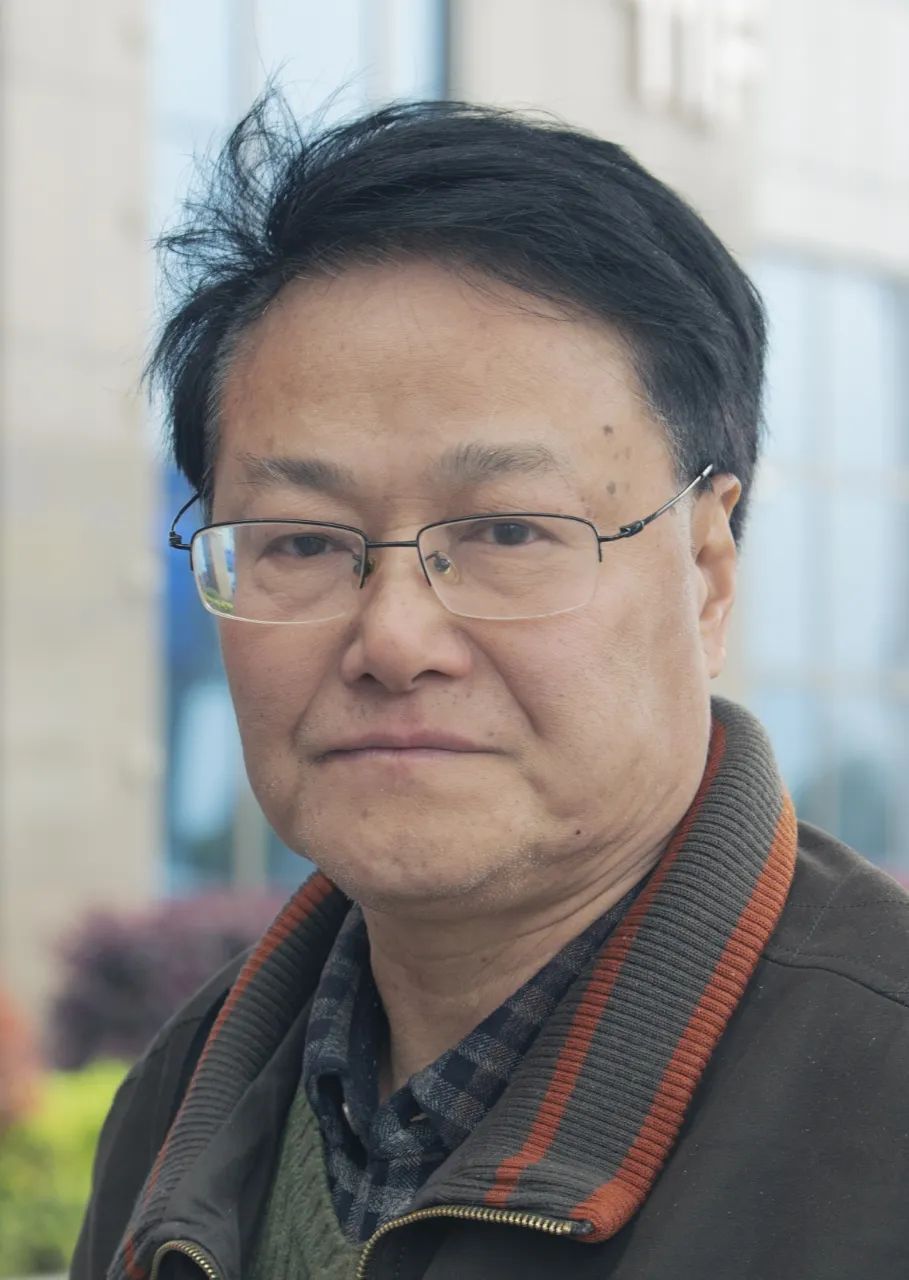
姜贻斌简介:出生于邵阳洞口县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左邻右舍》《火鲤鱼》《酒歌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窑祭》《你会不会出事》等多种。现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