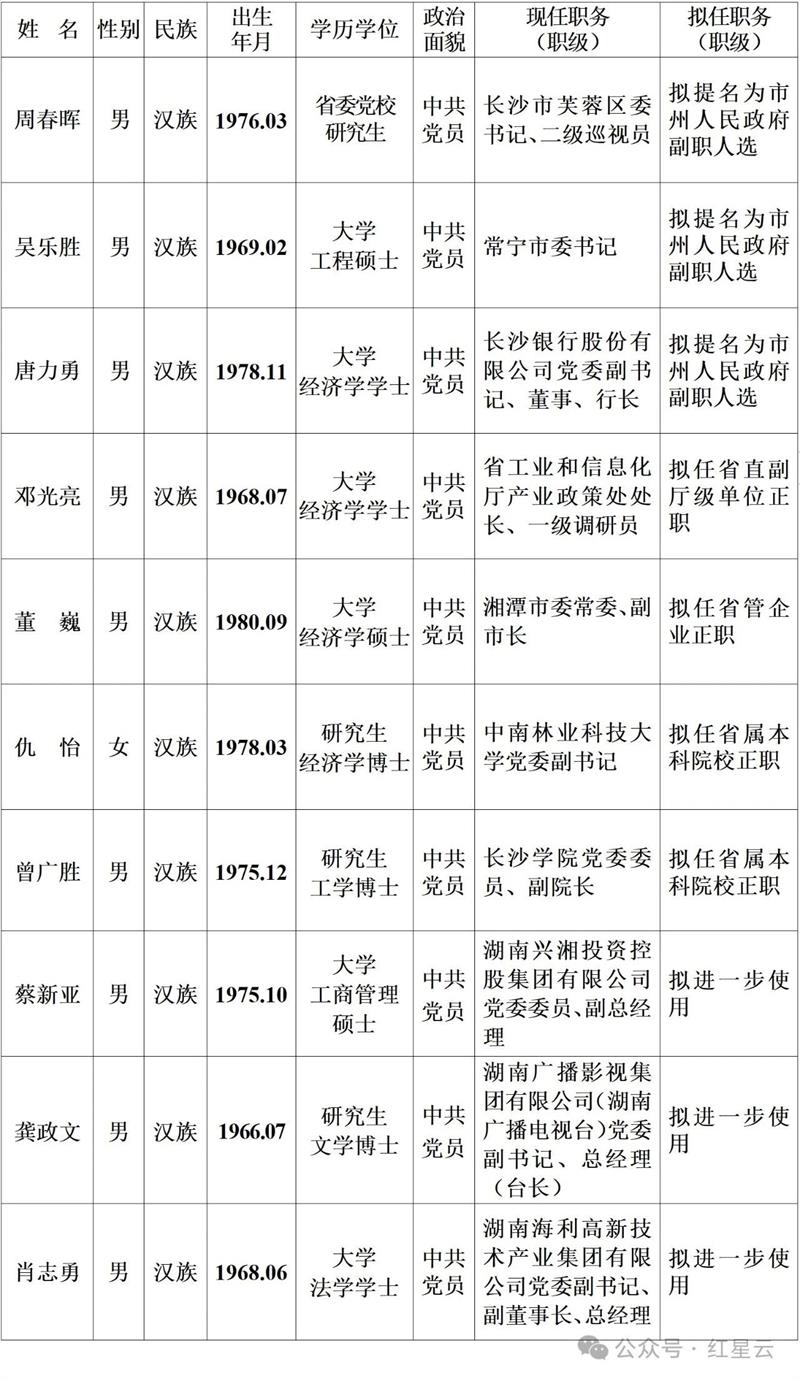一首五绝,让刘长卿家喻户晓。四十年来,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一直待在小学语文课本里,未曾挪窝:
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
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

短短二十字,描绘了一幅曼妙的风雪图,书写了一件助人的温馨事,渲染了一种幽远的清冷意,安抚了一颗惶然的孤寂心。文字清淡,感染力极强。品咂此诗,你的内心会云烟漫起,情绪拉得老长,久久不愿返回现实。
缺了此诗,唐诗定有遗憾。但若要自称为“五言长城”,刘长卿未免有些孟浪,与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王昌龄、高适、岑参等人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,他有多大的骄傲资本?
孟浪的,还有他的名字。长卿者,公卿之首也。据野史称,其名缘于司马相如,相如字长卿。而司马相如的名字又缘于蔺相如。都是个人崇拜惹得祸。
司马相如曾凭三寸不烂之舌,成功收复西南诸部,算是没辱没战国丞相蔺相如之名,刘长卿却没能复制司马相如的功业,一生碌碌无为。随州刺史是他的最高官阶,但很快随州就成为王师与叛军的拉锯战场,他没有报国心思,潇洒挂印而去。
因性格刚烈,好直道而行,刘长卿刚入职长洲县尉,就被同事诬告贪污。十多年后,他任鄂岳转运留后,因阻挠鄂岳转运使截留朝廷钱粮,再次被反诬贪污。
新旧罪名,全是莫须有。可他却背着这等污名,一贬再贬,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,连平反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有人证实他是贪了还是没贪,只因开罪了豪门,朝廷对他观感不佳,就先贬了再说。
第一桩贪污案,让他贬去潘州南巴。南巴在广东茂名,接近海南岛,在唐代是典型的蛮荒之地。“独醒空取笑,直道不容身”,刘长卿知道自己是吃了性格的亏,但他改不了,他没有同腐败官僚斗智斗勇的智慧与城府。
新旧《唐书》都没给刘长卿作传,多亏了他诸多诗歌的标题,才能推敲出他的部分行踪。比如《将赴南巴,至馀干别李十二》,就把起因、地点、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江上花催问礼人,鄱阳莺报越乡春。
谁怜此别悲欢异,万里青山送逐臣。
759年,李白随永王造反,兵败后流放夜郎,途中遇肃宗大赦天下,忙顺流东返。欣喜之情,被一首《早发白帝城》诠释得淋漓尽致: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之后,李白往返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,忙着走亲访友,760年春天,与刘长卿江上相遇。两人一个被赦,一个被贬,自是悲欢各异。
可不知什么原因,万里青山送逐臣,送了大半年,刘长卿还在离鄱阳不远的长沙,简直比蜗牛还慢,有《长沙过贾谊宅》为证:
三年谪宦此栖迟,万古惟留楚客悲。
秋草独寻人去后,寒林空见日斜时。
汉文有道恩犹薄,湘水无情吊岂知。
寂寂江山摇落处,怜君何事到天涯?
很显然,这首怀古诗的背景是秋天。诗人借屈贾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,不但满怀愁忧,更有愤怒交加。“怜君何事到天涯”,这个君不是指屈贾,而是指自己。先将自己当作客体,然后以主体的身份向客体发问。
那么他的愤怒从何而来?这是历代诗评家的困惑之所在。一般说来,蒙冤被贬,一开始就会爆发愤怒。时间久了,内心就只有忧郁了。忧郁能长久保持,愤怒则不行,因为愤怒是一种短暂情绪。
要解开这个谜底,还得从他的诗中找答案。《重推后却赴岭外待进止,寄元侍郎》正是解锁钥匙。重推,是指重新推荐。糟心的是,明明说了可以重新安排工作,朝廷却依然要他远赴岭南去等待结果,不愤怒才怪呢。第一时间接到这个荒谬的通知后,他便挥笔写下此诗,字里行间自然更加愤怒:
却访巴人路,难期国士恩。
白云从出岫,黄叶已辞根。
大造功何薄,长年气尚冤。
空令数行泪,来往落湘沅。
“老天爷啊,你何其寡恩薄情!以致人世间,长年饱含冤气!我只有把这流不尽的泪水,洒在湘沅往来途中。”诗人要去南巴,溯湘水而上亦可,用不着经过沅江。之所以湘沅并用,是他想起了蒙冤的屈原。
761年秋天,刘长卿接到“重推”的通知,距他被贬潘州已过去将近两年,而他还在“来往沅湘”,这期间他究竟去了哪里?
据《唐才子传》所载,刘长卿20岁参加会试,32岁才中进士,其间曾移居江州鄱阳避世苦读。另据史料推测,刘长卿晚年辞去随州刺史后,在江州隐居过一段时间。我们有理由怀疑,刘长卿在鄱阳一直都有别院。告别李白后,他根本没让“万里青山送逐臣”,而是窝在鄱阳等待时运。李白造反都可以赦免,他一个无罪之人,为什么不能赦免?这才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态。
可长时间等不到赦免通知书,他心里纠结呀,害怕呀,于是又挣扎着上路。然而走到南岭,“岭猿同旦暮”,凄厉的猿啼声从早到晚,又让他失去了往前的勇气。
761年,他在南岭过了春节,倍觉“乡心新岁切”,又眼看“春归在客先”,于是急忙忙往回赶。回到鄱阳没多久,朝廷终于准备给他重新安排工作,但却勒令他必须先赶赴岭南,履行上一次的朝廷旨意,这找谁说理去呀?这才是他“来往湘沅”之谜。
771年,时隔十年,刘长卿再次来到长沙,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岳麓山。麓山寺主持听说他要来访,特派僧人下山相迎。《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,过法崇禅师故居》一诗,详细叙述了他的参观路线,所见景物,及内心感受:
山僧候谷口,石路拂莓苔。
深入泉源去,遥从林杪回。
香随青霭散,钟过白云来。
野雪空斋掩,山风古殿开。
桂寒知自发,松老问谁栽。
惆怅湘江水,何人更渡杯。
这既是一首山水诗,又是一首怀古诗。诗人并未大发幽思之情,基本上是即景抒怀,有点像给麓山寺和尚交作业的味道,不是特别走心,没有《过长沙贾谊宅》那般情感激越,忧愤如潮,字字动人魂魄,句句摧人肝肠。
此诗前几句写景,后几句追忆法崇禅师。法崇禅师创建麓山寺,转瞬已是五百年。野雪年年落,山风日日吹,如今旧斋古殿仍在,昔人再无踪迹。以致刘长卿像个好奇宝宝一样,一会儿问带路僧:“这棵老松不会是法崇禅师所栽的吧?”一会儿又独自感叹:“法崇禅师去后,还有谁有他渡江时的无上风姿呢?这绵绵湘水,就像我惆怅的心情啊。”
这种感慨,若单看一诗,还真是不俗。但看得多了,就知道唐诗怀古思人,大抵如此。此诗只能算中人之作。能看出当时诗人放空放松的心情。若非如此,诗歌也写不得这么细腻宁静,清幽祥和,仿佛山中只有树梢风声与林间鸟唧,完全是一派无我之境。诗中的怅然,也类似少年强说愁滋味,算是唐诗的标配。
那时刘长卿正任鄂岳转运留后,兼检校祠部员外郎。官秩虽然不高,但职位比较重要,负责粮食财货的运输与分配。巡行江南道,路过潭州城,刘长卿度过了一段怡然自得的日子。山中碧泉,林间青霭,树梢白云,古寺钟声,旧斋野雪,抹平了他当年的创伤,滋润了他此时的心灵。这时即便再访贾谊故居,十年前的忧愤,不剩丝毫,也就不可能写出更上乘的诗歌了。
然而,这般心无挂碍的日子没过多久,刘长卿就再次被栽赃陷害。陷害他的是顶头上司吴仲孺。此人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,号称对大唐有再造之恩。在这样的豪门面前,刘长卿连开口自辩的机会都没有。多亏了当时的监察御史苗伾明察案情,多方周旋,刘长卿才得以摆脱囹圄,侥幸被贬为睦州司马。
刘长卿的一生就像一场漫长风雪,没有人知道他去世的准确年月,也没有人知道哪抔黄土、哪丛青草,是他的躯体所化。他就像一位“夜归人”,掩埋在大唐万千时光的尘埃中。
谢宗玉,湖南安仁人,一级作家,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,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湖南毛泽东文学院院长。著有《时光的盛宴》《末日解剖》《谁是最后记得我的那个人》等17部文学专著。